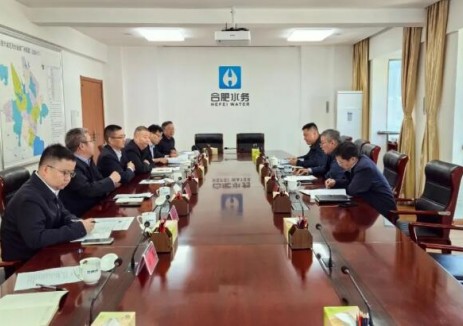作为仅次于二氧化碳的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甲烷排放带来的温室效应不容小觑。油气、煤炭生产活动中会有大量的甲烷泄漏。但按照国家标准的甲烷排放核算方法计算,目前我国能源行业的实际回收量和核算的排放量相比,差距较大,回收率较低。

碳中和目标提出后,相关配套举措正在加速推进。
日前,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在石油天然气、煤炭开采等重点行业试点开展甲烷排放监测。
作为仅次于二氧化碳的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甲烷排放带来的温室效应不容小觑。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做好甲烷排放数据监测是实现碳中和目标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意义重大。
更易治理的温室气体
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按照20年计算,1吨甲烷的温室效应与84吨二氧化碳相当,即使100年后,其暖化效应仍是二氧化碳的28倍,在短期之内是非常强势的温室气体。
据统计,2020年全球甲烷排放约5.7亿吨,人类活动造成的甲烷排放约3.4亿吨,占比60%。其中油气行业总排放量7200万吨,占人类活动排放总量的21%,煤炭行业总排放量4000万吨,占比12%,二者合计占比约33%。
“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甲烷是必须关注的重要内容,生态环境部文件的发布非常及时。”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庞广廉对记者表示,“在整个油气、煤炭生产活动中会有大量的甲烷泄漏,亟需高度重视。而这其中具体每个环节有多大的甲烷排放量,应该有一个比较可信的数据,这是控制甲烷排放的基础。随着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我相信能更好地进行排放监测。”
在美国环保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建宇看来,相对于二氧化碳,甲烷是更易治理的温室气体。“甲烷本身是一种经济气体,和其他温室气体相比,经济价值最大。国际能源署报告指出,75%的人为排放甲烷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回收的,而这其中50%的甲烷回收利用后是不产生额外成本的,因此我们认为甲烷是最容易治理的。此外,我们建立的碳市场,是给没有经济价值的二氧化碳赋予了碳定价,而甲烷本身就有经济价值,通过对它的管制,赋予价格,这给我们设定了一个很好的标签,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很多标志性的影响。”
排放数据可比性较差
事实上,我国正在建立甲烷控制体系,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已经开始了甲烷减排行动。
中石化从2011年就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发展战略之一,在温室气体减排、甲烷减排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2014年9月,中石油与其他9家国际大型油气行业巨头联合起来,成立了油气行业气候倡议组织(OGCI),开展了甲烷减排行动。煤炭大省山西也早已启动了采掘行业甲烷控排合作机制的研究项目。
据了解,不同石油公司的甲烷排放强度(单位油气当量的甲烷排放量)差别较大,我国油气行业甲烷泄漏率处于中等水平,约在0.4%—0.6%之间。按照国家标准的甲烷排放核算方法计算,目前我国能源行业的实际回收量和核算的排放量相比,差距较大,回收率较低。
在张建宇看来,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当前我们对甲烷排放的核算主要是通过因子法计算,但由于甲烷的逃逸性和扩散性,这种方法对甲烷实际排放水平有很大低估,并不能充分表征甲烷本身的泄漏量;另一方面,我们传统上并不是把甲烷作为温室气体来监测,而是作为一种潜在的危险源来监测,导致我们对甲烷实际的排放情况不那么了解。”
此外,即使是因子计算法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中石化能源管理与环境保护部副主任陈广卫曾对记者表示,当前能源行业对甲烷排放总量的核算,并无统一的标准或方法。“比如我们想跟中石油或者BP对标,看甲烷的排放总量具体在一个什么水平,但实际上我们几家的核算方法都不一样,或者采用的排放因子不一样,数据的可比性较差。”
应推动多种监测手段融合
此次生态环境部还在文件中指出,在区域层面,探索大尺度区域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监测。在全国层面,探索通过卫星遥感等手段,监测土地利用类型、分布与变化情况和土地覆盖(植被)类型与分布,支撑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工作。
多位受访者对记者表示,当前全球甲烷排放都在从因子计算法向以远程红外测量仪、无人机航扫、遥感卫星等为代表的实测法发展。
“核算和监测确实是不容易的。核算的标准、边界、指标以及处理数据的方式,都是重要的因素,但很多实地监测很难达到效果。”庞广廉坦言,“几种监测方式均不可偏废,可以在一些主要的地区,比如东北、陕西、新疆、四川几个主要的油气生产区内建立监测设施,以获取更加可靠的数据。”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大气部温室气体室主任毛慧琴指出,可以通过高精度的卫星遥感反演、结合“自下而上”的排放清单进行排放量反演。但甲烷排放遥感监测、监管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监测外,还要做好监管、评价、考核等工作。
张建宇指出:“我国生态环境系统目前主要是针对PM2.5、二氧化硫等传统污染物,监测标准和技术手段也都不是把它作为温室气体或污染物来监测,这是我们目前广泛应用中存在的弱点,甲烷监测还有较长的制度建设、能力建设的路要走。目前符合新的管理思想的能力,都主要植根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企业内部,且还处在探索阶段,没有上升到行政管理的具体实施层面,这是我们亟需加强的工作。”
 切换行业
切换行业






 正在加载...
正在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