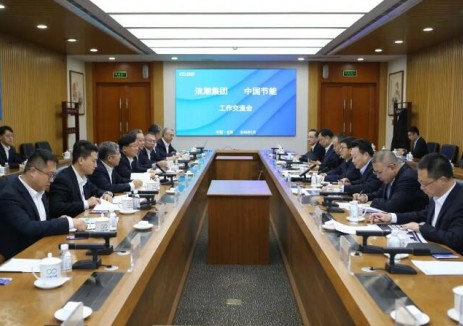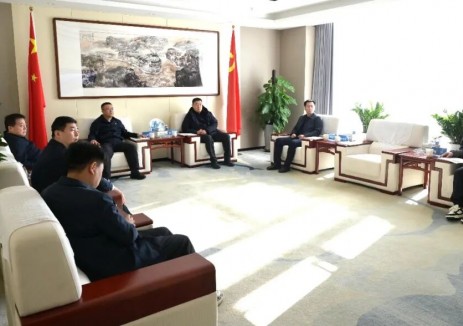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逐渐使用更加高级清洁的能源。当结构效应>总量效应时,即使能源需求增加,碳排放也有可能降低。实现碳能分离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碳经济学的4个关键原理
碳排放和气候变化之间存在密切的因果关系。人类活动,尤其是化石燃料燃烧、森林砍伐以及工业生产等过程,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增加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导致全球气温升高,产生温室效应。
每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都会对全球的温室效应产生相似贡献,不会因为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二氧化碳是一种长寿命的温室气体,在大气中停留的时间可以达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无论二氧化碳是在哪个国家、哪个时期排放的,都会逐渐混合和分散到全球范围内。因此,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是全球性的,而非局限于单个国家或特定时期。
减少碳排放所涉及的成本和收益往往不对称,且难以相互匹配。减少碳排放往往需要付出包括投资清洁能源技术、能源效率改进和减排措施等方面的成本。这些成本通常由减排的国家、企业或个人承担。然而,减少碳排放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往往不是直接且明显的。一是环境和社会收益往往分散在全球范围内,并不会直接回报给减排者,而是全球社会共同享受。二是间接的经济收益往往在短期内不容易实现,并且难以与减排成本相匹配。三是减排行为也意味着当前世代付出成本而未来世代获得收益,具有一定的利他性。
通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可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多赢局面。碳排放与污染物排放同根同源同过程的性质使得实现降碳减污协同增效具有可行性。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燃烧和加工利用,不仅产生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也产生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酚、氨氮等大气、水、土壤污染物。因此,通过采用清洁技术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方式来减少碳排放,也可以减少许多与污染物有关的排放。
碳经济学的12个基本事实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碳排放量与其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在经济发展初期,许多国家的产业结构通常以能源密集型和碳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例如重工业、石化工业等。这些产业对能源的需求较大,使用的能源往往是高碳的化石燃料,如煤炭和石油。因此,这些产业的发展势必会导致较高水平的碳排放。随着国家经济增长与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会有更多的能源被消耗、更多的工厂和交通工具运行、产生更多的碳排放。
新能源的装机容量不等于有效容量。近十年来,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经历了快速增长和技术进步,在太阳能光伏和风能等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装机不等于实际发电量。例如,截止到2020年底,中国风电、光伏装机在总量中占比达到24%,但全国风电、光伏发电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例仅为9%。这说明虽然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实际的发电量和能源消费仍然主要依赖于传统化石能源。此外,在考虑可再生能源电价时考虑“下网电价”,建议综合考虑新能源发电所需要的备用电源成本、运输成本、过路成本、系统成本、电网成本、匹配成本等。
部分国家和我国的部分地区出现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的趋势。这表明随着可再生能源实际发电比例的上升,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化石能源的发电占比并减少碳排。但也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助推了碳排放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部分国家将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将碳排放转移到了国外,从而出现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的现象。
我国消费测碳排放远低于生产侧。我国消费侧碳排放比生产侧低14%,这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意味着国内生产侧减排政策所带来的冲击可能会部分转移到国外,导致最终的政策效果弱于预期。这意味着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承担了一定程度的碳排放转移责任。政府可以在碳排放计算方法上进行改进,更加全面地考虑产品生命周期内的碳排放。
制造业虽然产生了大量碳排放,但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当前,中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约为40%,贡献了80%以上的碳排放。主要集中在电力、钢铁、非金属矿物制品这三个高碳排部门,且集中度在不断上升。因此,减少第二产业的碳排放是实现碳减排目标的重要方面。然而,减少碳排放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可能会增加生产成本,对企业的经济竞争力产生影响。因此,减碳与经济竞争力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
我国高耗能行业的能效水平已经达到世界先进。近年来,通过一系列节能政策的实施,中国的高耗能行业的能效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典型的例子包括企业节能低碳行动、阶梯电价、能效标准和能效标识政策、能效“领跑者”计划、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等。这些政策通过各种激励措施推动能效提升,也推动了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为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
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碳排放差异很大。由于群体收入、所处环境、职业类型;以及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不同个体以及不同地区之间产生的碳排量可能存在数倍的差距。因此,应当制定不同地区差异化的政策,根据地区特点和需求提供相应的支持和激励措施。对于经济相对滞后的地区,可以提供更多的投资和产业扶持,促进经济发展。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推动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和提升创新能力。
化石能源是减排的关键,但也是减排导致矛盾的关键。我国许多煤电机组正值青壮年,中国现有煤电厂平均年龄不到15年,大约50%的现有火电在过去10年内投运,85%在过去20年内投运,剩余设计寿命仍有数十年。过早放弃煤电机组将导致资源搁置和浪费。建议年轻的经济学家们更多关注CCUS,大力发展CCUS可以延长煤电机组的使用寿命,避免数十万亿资产的搁浅。二十大之后碳中和的技术路线由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改成了新型能源系统,这可能是“煤电+CCUS”这条技术支持路线受到了充分的重视。
国际上对化石能源的态度比较矛盾。我曾到访过非洲三个缺电国家,这些国家十分重视化石能源的世界地位,对多边机构不支持煤电和油气感到非常失望。此外,许多国家依赖化石燃料出口作为其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然而,随着减排行动的加强和全球能源转型的推进,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可能减少。由于能源出口国的能源市场份额和经济利益减少,地区之间可能发生地缘政治博弈,甚至引发紧张局势和冲突。
碳减排对中国能源价格的总体冲击可能不会太大。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随着清洁能源技术的进步和规模效应的实现,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其成本已经大幅降低,且竞争力越来越强。第二,中国政府积极推动清洁能源发展,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激励措施,包括补贴和税收优惠,进一步降低了新能源的成本。第三,中国正在逐步推进能源结构的多样化,减少对煤炭的过度依赖,包括发展核能、天然气和水力等替代能源。
发展权与排放权存在差异。前者是指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被允许排放的其他温室气体的数量,而后者是指各国拥有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权利。安哥拉等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缺电情况。事实上一个国家今天的能源可靠性和历史排放之间存在很大关系,不少先发国家已经占据大量碳排放空间,后发国家的排放空间就变得很有限,这种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排放限制会极大地压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
中国有望尽快实现碳能分离。2019年北京与浙江实现了碳和能的“强分离”,部分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或省内能源供给结构较为清洁的省份实现了碳能“弱分离”。碳能分离背后的机制是用能结构的转型。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逐渐使用更加高级清洁的能源。当结构效应>总量效应时,即使能源需求增加,碳排放也有可能降低。实现碳能分离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有助于减少对传统高碳能源的过度依赖,提升能源供应的可持续性,并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它还有助于推动绿色技术和创新的发展,促进低碳经济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除此之外,对降碳减排提出了两点建议。其一是以能源保供为先。将代际减排成均等化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举措,即为实现社会总效用最大化,减排的边际效用、影子价格以及碳价格的现值在不同时期均应相等。随着未来需求侧产业结构越来越轻、供给侧越来越富,后代能够更多承受比较高的能源转型成本,同时技术进步会使得未来有新的技术出现。因此建议当前以能源保供为先,不必提前担下未来几代人所有的减排压力。其二是建议国际上将碳预算分配给最不发达的国家,在多边机构之间实现总体碳中和,从而在降碳减排的同时保障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权利。
 切换行业
切换行业







 正在加载...
正在加载...